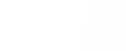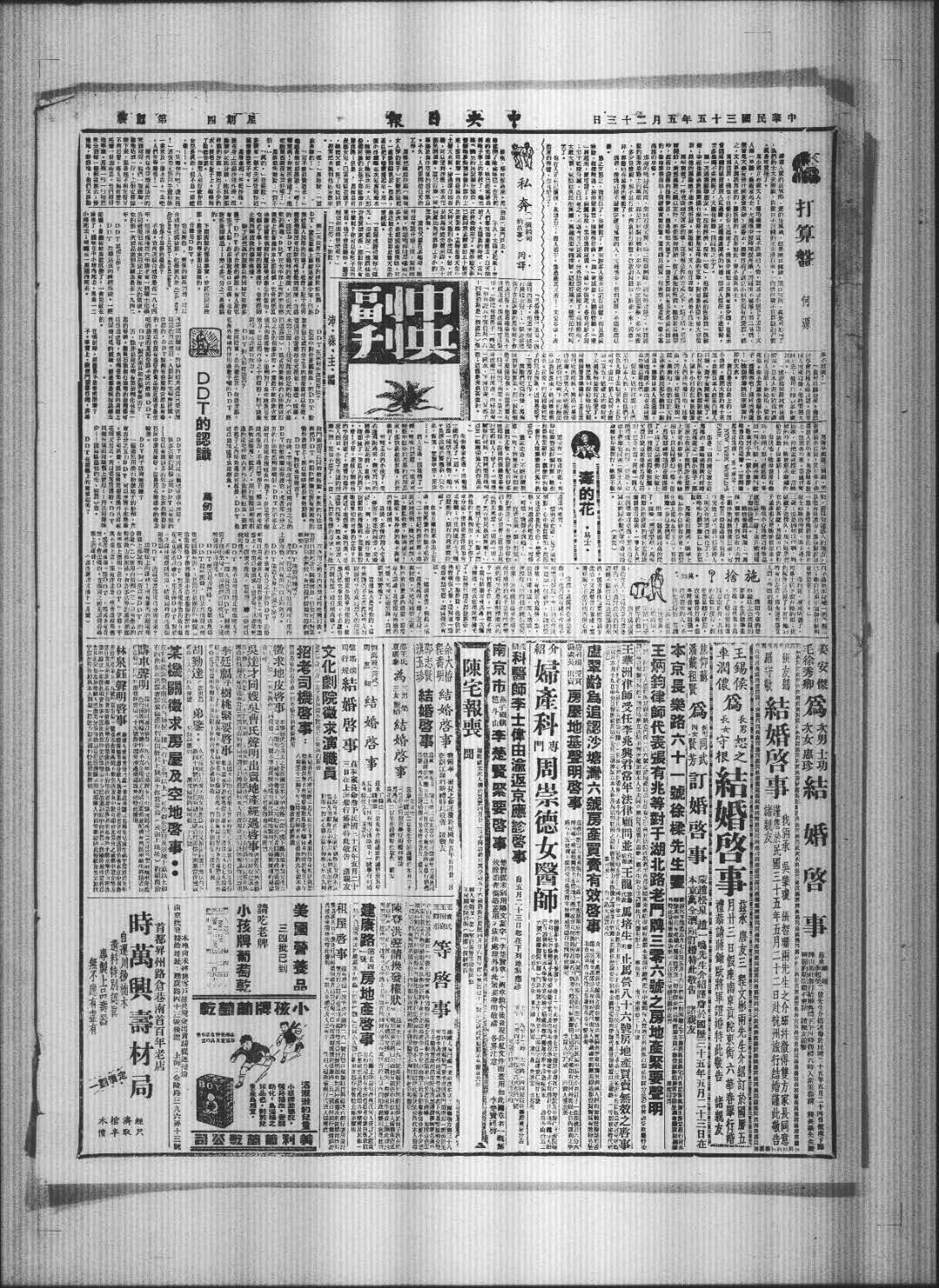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让书人重的是气节,爱的是国地,如果开口钱钞,闭口玉帛,真是可耻怀了我们的士大夫阶级,自从口不言钱的王夷甫以来,一向维待着不打算盛的习价,眞是可爱极了。
某小姐立志嫁文人;偏巧礒一位不凑趣的八物,对道足小姐下了忠告:文人第一系麟,艺术家名士,大概很少按时理发洗澡,否则便不风雅;第二是穷,庆曾见文豪有过什麽黄金美钞?这番话,总算打消了这位小姐莫须有的爱慕。德之,文人是郦该马虎的,应该穷的,若非如此,便不是眞名士。
写到这裹,我也不自觉的伟大起来了。我很少砾知口袋里有多少钱,也从未曾因为钱的原故跟别人红过脸,这种豪迈潇洒的气概,虽晋人复生,不过尔尔,
至多是晹不多酒罢了,大概也舁得一个高雅之士了。第一次遇到苏联朋友,「没有经济,没有一切」,他很认真的告诉我一个敎条;幸而也读过几篇闱扬什麽克斯什麽斯基理论的文章,对这番话还不曾大感务讶,然他的议验总不能使我折服,无论如何,文人而打算盘,总是不高雅。
两年前做了一件荒唐而又奢侈的事:在登报公告的方式之下,结了婚。从那畴闶始,渐感风雅之难以支持,亦从那时开始,做了风雅的叛徒。虽尚未为钱争吵,然而口袋里的法币目,总是略知大概了。一个月里面只有五天是接近困的,余时都很清明;我确隡实赏知道,这些钱只能买一包香烟,或者吃一顿不甚高雅的早餐。
那时的战局眞沉闷,忽然石破天惊,第二战场开辟,诺曼底登陆了,仅我震惊的并非是战士的勇敢,而是打算盘时胜利,多少人,多少武器弹药,多少飞机,多少登陆艇,那不是打仗,简直是打算盘。这敎训最难忘,鲜花一束,浊酒一杯,算盘站在风雅的的了。
忧·我想,像我这样不谱歙字硬充风雅的人,大概很多,想到这,不禁憋然以
思之又思之,我明白了,也解脱了,原来许多人并未忘记打算盘,而且加减乘除,梁栎精通,拚命做贪官,刚积作奸商,「加」有成数,大翻而特翻,「乘」将起来,便可观了;偷漏税,黑市裹做买卖,「减」少损耗,各有巧妙不同;至于干股分赃,古巳有之,不过今日之新富,分外除得干凈罢了。高雅余生,大澈大悟,气节原与民生无,风趣也要金钱撑騕。这般好风光,我要拍手呵呵笑了·
也有人正在记烂帐,攻城若干,杀人若干,制适难民又若干,未免多事,政治家的算盘,你也配打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