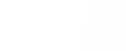报刊










摘要









廿八年春,我由西安至成都后,遇见在南京住家时的一位邻人,才晓得那位叫珍卿的族妹,在南京沦陷诗卽死于敌人:魔手中了。究意怎标死的,他说不上来,丙为他也是间接而又间接地得到此消息的。イ管是怎麽死的吧,死总是死定的了。始了这消息后,我非常悲痛,心田上好多日子都为她的影像所盘源,午夜梦囘,往往彷彿见她血肉模糊地倒在我的榻前,使我无法再熙然成寐
岁月转移,她时影像也就在我心田上淡了下去。最近囘到南京,得知她死时的详情,对于她的记忆才又鲜明起来。
论家族阅系,珍卿与我这一跃,正好还居五服之列,而且因住地相邻,所以对于她的家庭情形知之甚稔。在这个少女的生命史中,几平无一页不是充满着舌痛与艰辛,想起来益发增加我她的哀悼。
珍卿的父亲是个半生被关在「而子」妻春育时人,幼年时虽曾为三四个「底下人」扶銮保驾股地照护过,这祇是更剥削他自我能力发张的机曾而已。在十几年的丰衣足良中,却没有人对他正当的敎育略加关。成人以后,低能得近于白痴,与人晤对都呐吶不能出一语,更无论立身处世了。于是到了他这一代,便由戾屋地产变卖进而依今天卖点书画明天卖点家俱维持生计了。要说他天生无能,这常然是天大的冤枉,从一件事上就可看出他的聪明处来:大概因为关在「笼中」的生活太无聊的缘故吧,他就常以拆刘纩曰娱,久之,工具悉,竟进而长于修理钟表了。他虽有此手艺,在迫不城之时,犹不愿以此一技一长而正式「下海」,盖坚认一吃手艺饭」总非宦家后代宜爲;偶然为人修理时计,也仅烟卷若干喷吐喷吐已。其维持「体面」的苦心,可以想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