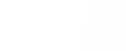报刊










摘要









『她已经和我说,是要休息去,此外没有别的话」『你不要管,她唤着你呢!我刚从她房里出来王大妈囘答就走了;没有其他的话。
等她去远了,我推开绣枕,走到母亲房裹倒使我一惊,睡在床上,桌上仅仅燃了一只烛,我从来没有看见她有过这样。 是十分憔悴,眼睛闭着,嘴唇惨白。 我轻轻走近她,站着,她脸上完全没有血色,满面戚容。 『母亲,」我低低的唤了一声。
「我的孩子,』她应了一声。 我犹夷不定,不晓得她将叫我坐呢,还是站着。 她将手点着,使我在床沿上坐下。 我遵命,听她将讲些什么,我心裹暗想,大概她又在想念到异国去的哥哥了。 但是她却不在想哥哥,囘头瞧着我,低低的道:
『我晓得你的一切都不好,我的女儿。 自从你囘来,我就觉得你以前的那些样子都改了,你的神致不定,你的眼泪流得太容易,虽然你不曾道得一字,但是我晓得你心里,必定有难言之痛。 那一样错了呢?如果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孩子的话,不要性急,我嫁了两年,才给你父亲生下儿子。 』
我不晓得怎样和她说,我执了绣花帘上的穗子,来囘绕在手指上,理理我的思潮。
『说啊!」她最后很严厉的问我我瞧着她:那无情的泪,使我】个字也吐不出来。 它抽上抽下的,我想抽得断气了。 然后井为一阵入伏在母亲的被上,大哭起来。
『啊,我不晓得他是什麽意思?」我哭道。 『他说我和他是平等的!我不懂是怎讲!他恨我的脚,他说难看,还画了这样的一张,我也不明白,他如何会晓得?我从来没有给他看过我的脚。 』
我母亲坐了起来。
『和他平等?』她睁着大眼,奇怪的道·『他是什么意思?你如何能和你的丈夫平等?
『外女人是这样的」我呜咽着。 「是的,但是我们的人,不懂这益°你的脚为什么媭他昼橱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