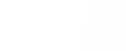报刊










摘要









我只觉少了一个熟识的面孔。
『四姨太太那裹去了?』我问。
我母亲唤过一个丫头,给她拿了烟袋,然后答道:'腊梅我叫她出去散步换空气去了。 」
从她语气里,我想还是少问为妙。 但是黄昏的时候我预备罔到儿时的粧阁去去睡觉。 老王大妈进,和我拆了头髪编辩子,她弄惯了的。 她咕噜着讲丁许多事,其中她告诉我说,我父亲又打算讨个新姨太太,是个北平女子,曾轻在日本读过书。 四姨太太听说这事,就吞了她最欢喜的翡翠耳环,她难受了一二天,才被母亲觉。
这女孩子几乎死了,唤了老医生来,也无用,他照样任手腕踝节里打针:邻舍推荐外域医院,但是我的母亲,以为没用。 外国人的事我们不甚懂。 外医生只晓得她们自己人的体气,简单而野蛮 如何能了解精通的中国人正切我的哥哥,中秋在家,他去唤了外国女生家。 她川很细的器具,探进叫姨太的喉曨,卽刻耳环出来丁 除了外国人,八人州称奇 她收拾好了器且,
伤长而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