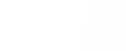报刊










摘要









无论什麽人,甚至於半大小孩子只要是中国的,几乎没有一个不会
打麻将」。打「麻将一,像这玩艺,嗜好於其中者是成着什麽兴趣,且
不说;只要想一想那用一张四方桌,分坐四个人·每个人都聚精会神
在许多小木块上面,呆呆的坐了几个篷头,简直使人想不出适励於中
国国粹的东西有一种怎样的媒乐意味。
这称牌,风行於国内的各地,一面到现在,实在的,是一种两人共
知的事实。其中—就在这所谓『第二巴黎」的商业最发达的上海,也就
是无数外国人来享幅的独有着租界的这地方,对於打麻将」,已现着
顾惹目的壮观。摸者这种小木块,不消款,官像们把它当做升官的楼
会,太太小姐们把它当做终目的消这,小买卖工人们把它当做梦力庭
辛苦的解放,即在自命处於智识最高阶级的文人们一什麻诗人呀小说
家呀至於什麽家什麽家之类,似乎有的也难免於大家『来四圈」,其实
『来四圈』而就能遇疗者,宝在是一极超乎普通的罕见。
总而言之,麻将牌,这玩艺醒成了肺病似的,和中国的无数民杂
成为不能分开的关系。
因此我想到;最会轻蔑中国人的那也剧於黄种的日本人,虽说很做
底的看透了支那人只有五分钟熟度』,然而究竟返不曾看到中国人的
这种恶习;伦若他看到,那一定在什麽时候谈到中国人便做出万分古
怪的鄙视和朝是的神气,把这「麻夥牌做为另一个支那人的代表名
释
其的,无西洋人怎样把娱乐走向袋刚,而中国人只管把他的
将牌」!
一九二入,八,二十六日,於上海,